立即注册
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没有账号?立即注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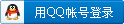

×
大约是在1969年河水结了一层冰碴的时候,我第一次回到我离别了20年的出生地。
客居黑龙江的我,十二三岁就记得我是出生在内蒙古奈曼旗的斑鸠沟。也曾为“斑鸠沟”这童话般的名字着迷,企盼。我想,那里的原野一定是飞着一群又一群的斑鸠鸟,沟里的石缝中隐藏着他们的家,一家几口人(鸟)在一起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天亮了,父母飞出去觅食,到晚上,一家子挤在暖暖的小窝棚里美美地睡上一大觉,睡醒了,唧唧喳喳地聊聊天(当然不是在网上),说笑话,破闷儿,讲故事,哦,那个美啊,真是给个神仙的日子也不换!
这是我从小就有的心中的故事,梦里几回有的童话故事,美妙,神秘,令人向往,永不忘却。
终于这一天来到了。坐在本家弟弟来接我的驴车上,车里专门为我铺上羊毛毡,走在崎岖的土道上,一颠一颠的,不得不用双手垫着屁股。聪明的弟弟明白了哥哥的意思,对我憨厚地笑了笑,于是“驴吉普”慢了下来,我也笑了。
秋风瑟瑟,满目荒凉。我开始环顾这魂牵梦绕的“斑鸠沟”,没有树木,没有流水。沟是有的,但不是山沟,是土沟。它们把大片土地分割开来,长长的,深深的。我知道这深深的土沟是流水冲刷水土流失形成的。当然也就没有了石缝里那暖暖的小窝棚,随之而来的是没有了原野里飞着的一群又一群的斑鸠鸟。深沟的上面自然是父兄们耕种的土地,玉米茬没有了,早已被父兄们刨回家烧火做饭用了。只有还在秋风中凛凛兀立的矮矮的谷茬、荞麦茬、小杂粮茬等,告示着这里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命根子”。
从班车(公交车)站估摸着走了一个多小时,弟弟说就要到了。我向四周望去,村庄在哪里啊?弟弟说就在前面的山沟里。哦,一座土房屋顶突然出现在我的脚下,“驴吉普”顺着大约有50度角的斜坡一点点轱辘下去,一座土黄色村庄出现了。
伯父伯母叫住了看家的老黄狗,把我领进了低矮的土坯房。哦,这里就是我呱呱坠地的老房子!
屋子里挤满了人,都是咱老仲家人是当然的了。人们看见亲人到了,前呼后拥把我请到炕里,给我铺上羊毛毡,毡子上面铺上小褥子,这是招待贵客的礼节。我不知所措了,一时不知说啥好。望望灰黑色的墙壁和灰黑色的屋顶,哦,这就是我出生的老屋啊,也许翻修过,也许还是老样子。屋地下挤挤嚓嚓站满了我的叔伯弟兄姐妹们,他们眼巴巴地瞅着我,一个个灰土灰脸,身穿不算“褴褛”却也不怎么好的衣服,只是女人们的头发抹得光光的,人们的目光里都带着一股热烈的企盼、仰慕、深情和兴奋。哦,这就是我朝思暮想的老家人啊,这就是因为族人里出了个我这样一个唯一的“秀才”而奔走相告的亲人啊!
终于有人出面了,他是我的二伯,他把屋里的人一一介绍给我,最后说:“事儿呢,就是这么个事儿!”
似乎这简短的“欢迎仪式”结束了。于是长辈们上炕了,鞋也不脱,分别坐在我的两边,自然地形成一个半圆,圆心处摆上了茶叶、水杯、暖瓶和纸糊的烟笸箩。这好像事先规定好了似地,侄媳妇做的是那么有条有理,自然从容。哦,这是要喝水抽烟唠家常了。其他人是没权利上炕的,还是呆呆地站在地下。另一个侄媳妇开始生火烧水了,土地当央立起两块黑色的土坯就是简单的灶,里面一撮子苞米瓤,火燃起来了,一根“绿豆条”(8号铁线)长长的,从屋顶上吊下来,钩着一把“爎壶”(专用于烧水的铁皮水壶)放进烟火处,等待河水沸腾。
这时,炕上的家人们开始说话了,中心发言人自然是最有权威的二伯,二伯是文化人,小学6年级本科毕业研究生,复员军人,族人和村中有个大事小情的二伯必须在场。“事儿呢,就是这么个事儿!”——二伯说上几句话就来这么一句。别人习惯了,我却觉得有趣。“这不嘛,今天伟国回来了,大家都很高兴。这几天呢,咱们谁也别出门儿(外出)了,明天到祖坟烧纸,咱们谁也不能缺,地下的听着,都得去!”
“事儿呢,就是这么个事儿!”“咱们老仲家是上几辈挑着挑从山东过来的,打我这辈算起来已经是第九辈了,事儿呢,就是这么个事儿!哎——!地下的听着,咱们老家是山东省登州府文登县仲家庄,都给我记住了!以后还得告诉你们的儿孙们!”“咱们的老祖宗叫仲子路,是孔子的得意门生。”说这话时,二伯提高了嗓门,第一次看见他笑,哦,是得意的笑,是自豪的笑。“事儿呢,就是这么个事儿!”
哦,这就是我的二伯,就是这千千万万个这样的“二伯”传承着儒家的孝道和文明,传承着仲氏家族的悠久历史!
我感动得热泪盈眶……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9-11-19 8:41:31编辑过] |  |Archiver|小黑屋|手机版|华夏仲氏网
( 苏ICP备2021045915号 )
|Archiver|小黑屋|手机版|华夏仲氏网
( 苏ICP备2021045915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