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即注册
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没有账号?立即注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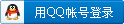

×

宝应的历史长卷中,“朱刘乔王”四大家族的名号如雷贯耳,却少有人知晓,在这四姓崛起之前,宝应的第一望族乃是仲氏。近日,我有幸聆听了仲氏家族后裔仲维林老先生的讲述,又结合自己的实地寻访,增长了不少见识。 仲氏一族源远流长,其始祖可追溯至孔门十杰之一的仲由,即子路,儒家文化的重要传承者。宝应仲氏的始迁祖,据传为五十二世孙仲七二,而五十六世孙仲兰更是家族中的显赫人物,膝下三子——本、棐、相,皆非等闲之辈。自迁居宝应后,仲氏迅速崛起,以医术闻名于元末明初,又以科举显达于明代中期。仲昶、仲兰叔侄曾为出入宫廷的御医,仲本、仲棐同胞兄弟高中进士,家族荣耀一时无两。 仲氏原居于宝应城内,在距城二十里的泾河乡下有一片方圆二十五亩的茔地,此地毗邻龙尾沟,相传沟中潜藏真龙,乃是一处罕见的风水宝地。仲氏先祖慧眼独具,认为此地可庇佑子孙世代荣华。传说一位阴阳先生因受坟庄人家怠慢,愤而施法斩杀真龙。他连夜制作四十九个稻草人,头戴斗笠,身披蓑衣,手持铁锹,一声令下,铁锹齐入龙尾沟,真龙毙命,风水遂破。此后,仲氏家道中落。虽为神话,却也折射出家族兴衰的沧桑。 随着时间推移,仲氏子孙散落四方,虽繁衍万人,却再难重现昔日辉煌,泾河祖茔亦逐渐被后人遗忘。难解的是,仲兰父子四人的墓葬并非同处一园。网上介绍说是同葬于仲墩,但据仲老所述,仲兰夫妇合葬墓发掘于泾河仲墩,仲本夫妇合葬墓则因大运河拓宽工程出土于河西,两地相隔数里。如此说来,仲老的说法更为可信。 据官方记载,1978年发掘的仲兰夫妇合葬墓出土墓志两合。1984年发现的仲本夫妇合葬墓出土了两具不腐尸及服饰、玉佩、状纸等文物。仲本官至陕西按察使(相当于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生前轻车简从,死后薄葬于野,证据确凿。仲兰家族墓园原为高土坡,如今封土已平,次子仲棐夫妇合葬墓与三子仲相夫妇合葬墓隐于地表,而河西处仲本夫妇合葬墓则已无迹可寻。 怀着对历史的敬畏,我决定探访仲兰家族墓遗址。网络信息显示其位于泾河镇钱庄村东部的砖瓦厂内,然而高德地图却无计定位。我骑车前往钱庄村,几经周折才得知旧砖瓦厂早已消失,眼前所见为易地重建的新厂。非我粗心,是不知厂址变迁所致。好在仲墩名气甚响,一问就得到了当地人的指引,方知已经骑过头了,只得返回重寻。 由钱庄路返至泾蔡路,皆为乡镇道路,一时竟找不到过往行人,总算见到了一位田间劳作的老农,复又得到河边一位钓翁的指引,我终于确认了墓园方位——竟是河边一片毫无标识的平地,与周围麦田浑然一体。手机定位显示,此处实为泾河镇大同村岳庄,与钱庄村相去甚远。墓园南枕黄浦大河(当不是古之龙尾沟),一座岳庄桥连接南北,过桥西行三十米即至。河北岸的圩上,一片麦茬中间,墓园遗址已化为平地,仅存两棵不足三尺的矮松(估计是新栽)。仲墩已无墩,龙尾沟也不知流向了何方。网上所称的两千五百平方庞大墓园,如今仅余几平方空地,道路因前日降雨而松软难行。 一方深埋地下的大理石碑默默矗立,碑面朝北,为近年仲氏后人所立。碑文被泥土遮掩,依稀可辨“宝应县仲子历史文化研究会”字样。因地面泥泞,我未能近前细看。抵达遗址时已过午后,阴云密布,细雨悄然而至。我用手机记录下眼前的景象,确认再无更多遗存后,便悄然离去。站在岳庄桥上回望,时针指向一点十分,细雨中的墓园更显寂寥。 这段寻访之旅,不仅是对历史的追溯,更是一场与时光的对话。仲氏家族的兴衰,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岁月的无情与沧桑。而那片隐于麦田的遗址,则默默诉说着曾经的辉煌与如今的落寞。 |  |手机版|华夏仲氏网
( 苏ICP备2021045915号 )
|手机版|华夏仲氏网
( 苏ICP备2021045915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