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即注册
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没有账号?立即注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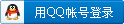

×

我与大哥仲伟习是叔伯兄弟,即同一个爷爷的弟兄。农历八月二十六日,是大哥去世两周年的忌日。在这两年的时间里,与大哥在一起的生活片段,时常浮现在我的脑海中。不写点关于大哥的事,总是觉得心里不安稳、有心事。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十月一日,大哥生于二伯父仲跻义家。他由于是长男,自幼温顺淳厚,受到爷爷与伯父叔父的格外钟爱。我在没出生前,母亲曾有意收其为嗣子。 母亲曾对我说过:“与你大哥一样憨。”有时的憨态让人喜欢,也可爱。大哥小时有些木讷、口齿不清,常在我家,随我母亲外出。有次跟随母亲到村东岭头(今海棠湾小区)拾草,看到下面河边土公路(今解放路)上正跑着一辆汽车,惊恐地说:“啊呀,你看嗫口大薄材(台),还跑。”吓得直往母亲身上穿的大襟桂子里头钻,好长时间才探出头来说:“过去了吧?”天快响时向回走,路边有块葱地,大哥可能饿了,说:“我吃块腾(吃棵葱)。”连着说了好几遍,估计是:我吃棵葱可以吗?父亲兄弟四个,年龄相差不过四岁,都是一米八多的个头,个个身体壮实,面目端正,都有力量。大伯父在距离许家庄三里的集后村杨姓地主家做长工兼管家,处理杨家的大小事物与日常生活,可谓事无巨细,尽心尽力,全心全力,以至未顾及个人问题,没留下后人。大伯父有次回家,对二伯父说:“老大已十多岁了,应该上学了,我在杨家做事,吃够了不识字的苦。”这样,大哥便在五十年代中期,在许家庄北方五华里的大郭村上高级小学,学制六年。在快毕业的时候,正赶上三年困难时期,饿的路都走不上来,同行的同学到路边的萝卜地拔了几个萝卜,给了大哥一个,那萝卜特别辣,吃了后眼前直冒金星,路也走不动,只得回家。从此辍学在家。 老家的前边是大哥家,大哥家的西边是一片小树林子,傍晚时分,林中的各种鸟儿唧唧喳喳叫个不停。我隐隐约约记得,大哥拿着弹弓在林子中仰头打鸟儿,敏捷轻巧地在林子中穿来穿去,我在边上拿打下来的鸟儿,打的少时,用火烧着吃,略多则炒着吃,那鲜味至今难忘。 家在本村后街住的二舅,常来喝酒,父亲不喝酒,大哥陪着,有时我也喝一盅。 母亲比大舅年长七岁,姥爷去世早,三位舅舅都是母亲带大的,对母亲的感情都很深厚,经常来我家。二舅叫许延祥,曾在新疆当兵,转业到克拉玛依油田保卫处,随军的二舅母不服水土,经常生病,只得全家回五莲。 当时住在村里打村南水库的县委书记卢星文,白天与民工一样挑土干活,晚上开会,非常欣赏二舅的人材、口才、工作能力,即提议任命为村大队长兼村南水库工程指挥部负责人。从县委书记到普通民工,全部上阵加入一线劳动,使人想起那个红旗飘飘、歌声嘹亮的火红年代,激情燃烧的岁月。由于措施得力,人人争先,大干快上,使工程提前竣工。这其间,大哥与二舅在一起,日夜奋战在工地上。大哥也因表现突出,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山东阳光集团(原五莲热电厂)至今在用这水库的水,使居民取暖及工业生产。 为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一定要根治海河”的号召,五莲组织了挖海河民工营,由二舅带队,大哥积极报名,参加了治河大军,发扬刀山敢上、火海敢闯的精神,凭着一把铁锨、一辆小推车,疏通了海河流域,根除了水患,使一千多公里的海河沿岸人民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 回村后不久,便开始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五莲第一中学的一位哲学老师王先鞭造了县委的反,做了县革委会主任,他在我们村的学生也做了村革委会主任。 记得我六岁的那年冬天的一个上午,在村西许氏家庙的大院里,召开了社员大会,还有一个排住村“支左”的解放军也参加了会议,他们排列整齐地坐在会桌前边。靠西院墙的墙根下,几个村干部排成一排,低头弯腰,要成九十度,两手指要触地,脊梁上用浆糊贴上大字报。二舅也在被斗之列。 我在家庙大门前的石板桥下玩沙丘,看到这一切,跑过去将二舅身上的大字报揭下来,被人抱到一边。不过二十几分钟就结束了,就像演员下台卸装一样,干部们还是被“大叔”“二爷爷”地称呼着谈笑风生。按现在的话说,是做秀,走过场罢了。 现在觉得,当时的这场运动,就我们村而言,斗争的对象主要是门衰祚薄而又不具口德之人与欺街骂巷横行乡里的蛮霸之徒。 我家七十年代前的两间老房子是两间,底矮的门框,常碰进出人的头,两扇门板上全是坑坑洼洼的麻点,那是被我小时用称勾子剁的。进门对面是用两页2×0.5米的石板垒起的碗框架子,右边是灶台,左边是小拐炕,我与父亲睡;没有壁子墙,只有用土坯垒砌的1.5米多点的半壁子,晚上将煤油灯放在上面,里间外间都能用,上边是约有一搂粗的榆木梁。里间的右边是炕,炕的西北角还拐出一块,直到屋北墙,象刀把;左边是一台柜子,那是母亲的陪嫁品,母亲去世后,柜子也散了架,看起来,做工精细。二舅来吃饭时,盘腿坐在客座,父亲在炕头,母亲在下首,大哥蹲在拐炕沿上。桌子上最多四个莱,一般就两个,二舅从不吃,只拿筷子在盘里一蘸,又放下筷子,有时喝盅酒,拿着筷子说半天话再放筷子,父亲也一蘸,再放嘴里一放,大哥少吃点,大多都被我吃了。 二伯父在几个父辈的相助下,盖了三间新房,那是准备给大哥娶媳妇用的。大哥独自住老房子,因距我家近,来去方便。每晚都玩至夜深才走,并说:“一晚上一个团长。”因衣被单薄,夜深困了,躺下蜷缩着就睡了。 这天晚上,二舅带了瓶白酒、红纸、毛笔与墨汁,让大哥写大字报,二舅口才好,说话很有鼓动力,但没文化,不会写字。大哥虽然高小没毕业,但有文化基础,这几年与二舅在一起,从串联、演讲等方面,水平都得到提升,而且是二十多岁年纪,正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时候,何况二舅还在一边大力支持与褒奖,并说:“要下地狱有我,不用外甥你,我就不信天能塌下来!” 第二天早上,二舅与大哥把昨晚写的大字报贴了北大街墙上一大溜,三三两两的人在围观,有的还念出声:“某某干部与四类份子打的火热,不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与牛鬼蛇神沆瀣一气。” 这样每晚都写一大摞大字报,天明贴出去,人的“左倾”或“右倾”,成为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标志。大哥身边集聚了一群青年,有的不知从哪弄的旧军服穿着,手拿报纸与啦叭筒,随时演讲、歌唱,记得大哥经常哼唱的是:“毛主席啊,天上的群星啊永远朝北斗,地上的葵花呀永远向太阳……您亲手点燃的文化大革命的烈火,把我们百炼成钢……”。 有一天父亲下班回家,说:“今天碰到县委卢书记,也被打倒了,用拖车拉砖,两位监督人员帮他推车。”大哥的造反队又成了右倾。 晚上在许氏家堂屋大院里召开社员大会,在大院中央放一张桌子,一条桌子腿上绑一根木棍,棍子上方挂一盏汽灯,有人将汽灯打汽后落下灯罩,调大气门,会场顿时亮堂起来。先高呼口号:“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打倒走资派!”等等,接下来在会场西北角开始打一个独姓人,因他嘴贱,说了句:“社会主义大改变,冬至吃不上顿地瓜面。”“社会主义刚露头,(每人发)三尺布票二两油。”结果被打得用牛粪筐抬回家。其实是有宿怨的人借机泄私愤。 革委会主任底气十足地咳嗽一声,用手指着在会议桌边低头弯腰的造反队二号人物仲跻道说:“你这样的小老叨还想挡住历史的车轮子吗?简直不自量力!下面将右倾分子仲跻道押一边去,让他捞稻草,抹油水!”两个背枪的民兵推攘到西院墙边,用一根粗稻草绳子在仲跻道的腰上缠绕一图,一个松,一个拽,这样仲跻道像轱辘子的钻一样,一会儿左转,一会儿右转,围观的人们都哈哈大笑。 有人又给汽灯打了气,革委会主任拿出笔记本看了看,说:“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动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让我们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同坏分子斗争到底!怎(咱)这个地方安了打仗铺,谁说来和怎(咱)打,怎(咱)就跟他打,一直打到他们完全失败、彻底垮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主任略微一顿,话锋一转一转继续说:“仲伟习!你仰抗着头像大爷似的,今晚,你准备怎么着吧!”这时坐在会桌边的父亲一手抱着我,一手提着凳子站起来,说:“主任弟,你准备把孩子怎么着吧?”二舅也站起来说:“是啊,说清楚,准备怎么着办?”这时的会场鸦雀无声,大多数人都站了起来,伸长脖子,瞪大眼睛,等着看热闹。 主任看到村里许、仲两大家族都有人站出来为大哥说话,都是八辈子贫农,还都是旺族,便笑嘻嘻地说:“自家孩子,亲戚道理的,我不可能把他怎么着。”站起来的社员们又纷纷坐下去继续开会。 二舅与大哥依旧在写大字报,大哥也在写大字报的过程中练就了一手能拿出门的毛笔字,春节时,人们都去找他写春联,口才与组织能力也更上一层楼。 春节过后,村革委会通知大哥到社办工业上班,每月工资9元,向大队交7元。二舅在我家对大哥说:“可以,趁年轻,出去闯荡一下,也不错。其实他们是斗争不了你,你还不安分,才把你扒拉出去的。”父亲也嘱咐一番。 从村到公社5里,到大哥上班的社办工业前店后厂是4里,具体工种是打铁,主要是煅造锨镢锄镰,以供各大队生产使用。 那时会多,洪凝公社又是县委、县革委会所在地,县里的一些集会、游行等活动,大哥都积极参加,并被推选为呼口号、写大字报等方面的主要人员之一,不久即被任命为社办工业团支部书记。 与大哥一起上班的一位老师傅是仲因村人,非常看重大哥的人品与做事能力,对大哥的演讲更佩服得五体投地,登门为大哥保媒提亲,女方是他的邻居,在村里还是识字班队长。二伯父表示:“出身成份没问题,我家穷点,人家不嫌弃就中,抽空让他们验验。” 在洪凝大集上,大嫂不高不矮,不胖不瘦,体格匀称,面目端正,正与另外两个要好姐妹在人来人往的集市上。大哥正在打铁,便解下皮围裙,与媒人一起出来了,青色凡尼丁裤子,膝盖以下部分被打铁溅起的火星烫得全是大小不一的窟窿眼。媒人介绍后,大哥的眼睛略微一扫,拿出烟抽着。大嫂倒说:“脸上的灰也没洗,就是个嘲巴。”与两姐妹笑哈哈地远去了。 找了个好日子订亲,女方来两女客、两男客,男客在家喝茶,大哥与媒人陪女客到街上大社(供销社)买东西,就买了一双鞋、一对手巾、一个脸盆,大嫂割了一块褂子布料等。押合子钱(彩礼)9元。 大嫂她们走后,大哥在街上分烟卷,有几个长舌妇唧唧喳喳地说:“这么俊俏的小伙,竟找了个脸上有几个黑芝麻斑点的媳妇。”还有个说:“伟习在村里是数得着的青年,太可惜了。”有几个青年也跟着起哄。大哥便转身回家了。 晚上大哥对母亲说:“我怎么没看出来呢?”母亲说:“详细看,是有几个黑点,不碍事,叫壤壤叫的甜,听了真舒服。”大哥沉默了一会儿说:“明天去退亲。” 第二天早早到厂停了假,回家拿了大嫂捎来的一双鞋、鞋垫、腰带等物,来到仲因村大嫂家,对大嫂父女说明来意。老人沏茶倒水说:“来了先喝点水,吃了饭再回去,虽然几天,也是缘分。” 时间不长,大嫂笑嘻嘻地端上四个莱,老人也好喝酒,与大哥很对脾气,问了家里的情况,与大哥一问一答地聊着家常话,全没有退亲的言谈举止。 大嫂拿着包衬,里边是定亲的什物,送到村后不远处的小河边。大哥接过包衬过了河,大嫂在河对岸说:“钱在鞋里,别喝点酒拎打掉了。”说完转身回家了。 大哥抽着烟,望着大嫂远去的背影,坐在河边树下的一块石头上,想着大嫂一家人,老人掖在口袋里的一合金鱼烟也快抽完了,太阳已快落山。越思越想这事办得欠妥,遂决定再把包衬送回去。 大哥到村里的代销点买了两瓶酒、两盒烟,又来到大嫂家时,全家人都笑了。大嫂笑得格外开心,说:“一见面就说你嘲,还真嘲的不轻唻!” 母亲曾说:“先前见人家娶媳妇,非常馋,跟着直看到最后,从你大嫂来后就不再馋了。” 大哥是在新房子里结的婚,婚后一个月,父亲与四叔去给分了家。二伯父说家穷,盖不起房子,让老大住两间老房子,新房子再留给老二说媳妇。大哥大嫂虽不满,但无怨言地搬进我家前面的老房子。 大哥工作积极,办事认真,深得领导信任,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还被任命为仓库保管。 有个星期天,我到社工业仓库,看到职工领漆刷农具,说家中屋门年久腐蚀严重,倒一酒瓶漆回家刷门,揣兜里别人不会看到。大哥二话不说:“不行,都是有数的。”大哥让我去买了5角钱的猪头肉,一瓶酒,我也喝了点,吃完饭才回家。 过了一段时间,社工业成立农修厂(现五征集团安旭公司),大哥进入支部委员会,并被任命为副书记。 一年后,根据上级指示要求,公社成立工业发展交流办公室,简称“工交办”(后称经委),老书记调任工交办主任,大哥接任农修厂书记。 在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下,五莲农修厂也和全国一样,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洪凝工业以农修厂为依托,先后成立了建筑队、钢窗厂、附件厂等一批社办企业。在各社办企业工作过的职工,没有不知道仲伟习的。 1975年春,洪凝党委、革委会、工交办研究,决定在城北(现解放路与黄海路交汇处)由仲伟习筹建五莲县石子厂,给配了一辆自行车,还戴了块十五元的“钟山”牌手表,我还戴了会儿,放在耳朵上听了听秒针的“嗒嗒嗒”的声音。当时,在我们这个偏僻的新建小县城,是相当稀罕的物品。 石子厂,是后来号称江北石材产业第一县的拓荒企业,会计就是后期大名鼎鼎的李宗东,莲意石业公司董事长兼五莲石材工业局局长,也成就了一批声誉远播的石业老板。现在这石材厂就在仲家林前一里处。由于市场经济的大潮与国家对矿山开采的管控,现已是黄昏企业了。 八十年代初嫁到许家庄的一位媳妇,以前曾在石子厂上班,提起伟习大哥,最难忘的是他的讲话,至今还津津乐道:“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头顶蓝天,脚踏烂石,大干社会主义,艰苦奋斗,敢叫日月换新天!” 1977年春,在“反击右倾反案风”中,伟习大哥受到冲击,被停职赋闲在家。两个女儿也快到上学的时候,正有时间砸老屋盖新房,着手筹备所需材料,由生产队承建。 五一节后的一个星期天上午,我去看大哥的新房。还没院墙,屋东有条水渠,水库放水灌溉农田用的,屋内地面有刚打夯的痕迹,大哥独自一人在家,坐在一个半米高、直径约三十公分的三条腿的铁圆桌边抽烟喝茶。哥俩边喝茶边闲话。“这三间房盖的快,不到一月,手工费60元,就管了一顿散场饭。” 随后,用盖房剩余的三角葫芦头的石头干插垒砌了院墙,做了篱笆门子,算是独门独院,举家立业了。 大嫂因陋就简,在院墙角搭了几个简易小棚,养猪、狗等家畜。谷雨前后,也在院墙外种瓜掩豆,贴补家用。 1985年左右,在院中打饮水井,不承想,一米后挖到石头,给打井带来相当的难度。各位叔兄弟、左邻右舍及亲朋好友,奋战了一冬一春,最后,不得不打钎用炸药,又找了块略厚点的铁板盖在井口,上面压些石头,爆炸后的碎石飞不上井口来,等硝烟散尽再下井挖掘;再用小铁车的轮毂支架在井口上,替代滑轮吊运土石碎料,劳动起来,轻松多了。 冬季的农村,最宜储备而且数量最大的蔬菜是大白菜,冬天没过就吃完了。印象最深的是,平时都炒几个菜喝酒,这天晚上大嫂因事回家晚,又没备菜,便用油炸炒了一小盆花生米,大伙饿了,喝口酒,便像小鸡啄米般吃花生米,大哥高兴地说:“好,又做酒又当饭,还垫饥。” 快四十年了,还在使用这口井的水。 九十年代中期,大嫂致力于发展家庭养殖业,经济略有宽余,套起了院墙,盖了两间南屋。2000年后,又接盖了两间南屋,还将堂屋进行了装修,每月60元租给一位亲戚居住。这样的房子,本来每月租金应该400元以上。 1977年8月,大哥又被任命为五莲县联合运输办公室洪凝站站长。 我已是邻村联办初中二年级学生,班主任是位女老师,刚生产二胎,使人叫我到她家,问些班里的情况,说:“你作为班长,顶个副班主任,学习不好,没有说服力。现在打倒‘四人帮'了,教育制度改革,以后升学就业都需要考试,你头脑不笨,多背定义定理,不明白就来问我。”老师说的真好,很对,要执行。这样我就没时间到大哥家或单位玩了,全身心扑在学习上。 当时有句时髦话:“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做社会主义一代新人。”我对考高中没抱多大希望,想不到居然考取了,全校200多学生中,只录取了9人,而且还是全县招生的重点中学——五莲第一中学。 8月1日,我在蒙蒙细雨中进入一中。大门口有欢迎新同学入校的让人心热的标语,向前是平坦笔直的大道,两边是大小高矮均匀的松树;左边是几排高大整齐的平房玻璃门窗教室,每排教室的山墙上,都有一个大黑板,上面有毛主席画像、语录以及揭批“四人帮”的宣传材料等。下面有几个斜卧地上的黑板,上面有新生班级、班主任姓名及宿舍编号,一边坐了几个学生,如有不明之处,便询问。 宿舍是10人一间的双层床,每张床上都有一席稻草帘子铺在上面。我只带了毯子,正好铺一边,盖一边。 午休时,有学生忽然带大哥来到宿舍,我立刻从床上跳下来说:“哥来了。”大哥笑容满面地看着我,说:“听说你考上高中,今天来报到,我过来看看,条件太简陋了些,我在一中后不远处有三间房子,摸可以住到那里,有时可以骑车回家吃饭。”我高兴地与大哥边走边说笑,向这房子走去。 从学校大门口向北,是洪凝村的村街,有四米宽。三百余米后,一个十字路口,向北通向洪凝村里;东西路段宽有二十余米,向西左边是洪凝公社建筑队,约占地八万余平米,西邻就是农修厂;右侧是五莲县糕点厂。向东二十余米,左侧是民房,右侧是两扇大竹门的大门口,再向东又变窄成村街了。这里便是房子的所在地了。 大门口是用块石铺就,水泥抹缝,中间有块凸出地面十公分的石头,挡大门用的。 进入大门口,右侧是院墙,左侧是两排各九间的平房。前排是三个公社党委副书记的住家,最西边三间,住的是管工业的陈秀山书记,再向前,是一个空旷的大院,约三百平米,西南角是两间分男女的厕所。后排与前排之间有个三米的门口,没有门,进门口左边是一棵亭亭如盖的国槐树,树后向东六间屋,是运输管理站的办公区。再向东,便是大哥个人使用的三间房,东边是一堵很高、拔了好多台阶的石头墙,上边是糕点厂职工宿舍。 进门右边是水泥抹面锅灶,一边有一台柴油炉子,上面有口小锅,这在当时很罕见。北墙边有个饭桌,桌边有几个交叉子、板凳,还有些简单的餐具。西里间堆放些乱七八遭的杂物。东里间迎面是一张三抽桌,上面有猫眼闹钟,有一盘炕,北墙两边有两张单人木床,东边床上,有卷起的铺盖。看到这些很高兴,说下午下班搬过来。 下午与学校打了招呼,下班后把简单的行李背过去。 大哥没走,带我到农修厂北边的供销社,买了一瓶酒、一斤猪头肉,还有一个鱼罐头,又到建筑队伙房打了两份莱,哥俩回屋喝起来。 边喝大哥边说:“洪凝街人都称这里叫老马棚,外面人都叫运输站。据说县委县政府1950年迁洪凝后不久,就盖了这两排房子,套了这个大院,饲养骡马,存放大车,运输货物用。后来有汽车了,骡马大车用的很少,现在又做了运输站,单位小,事少,到轻松。”这时,我听到有人进院的咳嗽声,便说:“有人来了。”大哥说:“是后边老董,人称董老黑。常来。” 老董推门进来,“站长来客了?”大哥答道:“是我弟弟,在一中上学,以后就住这里。” 老董从饭桌上的金杯烟盒里拿了一只烟叼在嘴里,又到里间拿一把椅子坐下,把一只鞋用另一只脚一碰,脱了鞋,把脚放到椅子面上,半蹲在椅子上,点上烟一抽,口一张吸进去,又慢慢吐出来,神态很自得。 我添杯茶水递给他,这才看清这“董老黑”的确黑得到家,十足的一个印度人,衣服也有些破烂,看来日子不宽裕。 大哥让老董喝酒,他说已吃过饭,不喝酒。并说:“原先叫宿舍,现在你兄弟来,这里也是家了。” 我们一边喝酒,大哥继续说:“据说,从太爷爷时候起,我们家就没有文化的人,沾新中国的光,我有点文化基础,你考上高中,毕业后,咱家你学历是最高的。毛主席说:‘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有文化与没文化,做事是不一样的。” 我回去早饭后到校,发新书,交2.7元书费,这是上学第一次交学杂费。从此,开始了高中生活。 一天中午,我回去吃饭,见村里的仲崇健来了,还买了酒菜。他是我小时的玩伴,长大后当兵了。两个人亲热地拉拉手,问了什么时候复员的等。崇健说:“已复员四个多月了,在生产队当社员,父母体弱多病,无钱取药医治,生活无着落,想找伟习叔谋个职业。昨天在咱队场里,与队长许延武打了一架,还把他摔倒了。” 大哥说:“这边已满员。我昨天与拖拉机站站长一起吃饭,他与我关系很好,我说话不太方便,最好找住前边的陈书记,他最喜欢生吃花生米。”指指我:“让他领你过去。许延武不同意,你可找你伟满二叔,同去找革委会主任开介绍信,他们很处得来,越过生产队这一关。” 这位陈书记为人严肃,站里的人问“陈书记好”时,他总是在噪子眼里咳着、鼻孔中哼出个“嗯”字。对我则青眼有加,总是笑嘻嘻、慢慢地说:“去上学?” 我好看书,陈书记也喜欢看小说,我从学校图书馆借书,拿着向回走,他拿着看看,并说看完他看。有时借书他先看,我再看,有时也到屋坐坐,谈些读后感,时间一久,便因书之缘,成了忘年交。 几天后与崇健到陈书记家。我也是第一次来,陈书记还沏了茶,我们说明了情况与来意,陈书记让回村开介绍信,到工交办公室交郭主任,这事就成了。 有天晚上,大哥说:开了一天“双打”动员会,下午揭批“四人帮”罪行的发言时,咱队仲伟俊二哥的发言,感动了全场,他哭得嘴唇哆嗦,胡须上都是眼泪,公社大礼堂鸦雀无声,他说:“‘四人帮’把我们家祸害毁了,我四弟伟助玩笑地唱了句“毛主席躺在了天安门广场上”,被许延武立时汇报了大队,大队干部与驻村工作队赶到生产队,召开社员大会,伟助低头弯腰,被两个背枪的民兵看着,中午戴大纸帽子游街,许延武带头呼口号:‘打倒仲伟助!’晚上召开全村社员大会,继续低头弯腰,进行批斗,一天没捞着吃饭,最后被打得动弹不了,逃到东北躲了一年多。大哥伟高与他划清界线,五弟伟勋教学不敢回村,最后斗三弟伟公,白天在生产队干活,中午戴了九十六斤的大纸箱子游街,晚上召开社员大会批斗,真是生不如死。民兵在家门口站岗,只准老老实实,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大年五更,逼的我八十多岁的老娘逃到松荒顶死孩子岭上,望着千家万户的灯火,听着大年夜的鞭炮声,这个生育五子四女的老人,几次欲寻死路……”大哥有些肯定地说:“看来呀,咱庄的革委会主任倒台定了。” 我也说,学校在大操场召开大会,党委书记韩俊三讲话说:“‘四人帮’在五莲县的爪牙王先鞭……王先鞭坐在主席台的旗杆下一个方凳子上,不时仰头看看旗杆顶上的大高音啦叭,有些若无其事,处之泰然。” 大哥认识王先鞭,对他的演讲非常钦佩,几次赞不绝口。说“文革”时,他与诸城王敢冲、安丘王敢闯,号称昌潍“三王”,省里有名,中央有号,都是“九大双代表”,曾组织“红卫兵”,高举红旗,自备行装,一路高歌,一路口号,列队进京,受毛主席检阅,各自与毛主席合影。所以很自信。 据说,王先鞭只是被撤职,回一中不久,又回了临朐老家。后曾设民办小学到高中学校,招收百名学生,90%考取大专院校,后再无消息。 大哥不常回来吃饭,也有人来找他喝酒,星期天时,定让我也喝点。来找我的同学也渐渐多起来,大哥也认识了不少。 有个周六中午,大哥说青岛下午来客户,吃晚饭后一起回家。下午四点,大哥用自行车带我到县城第一饭店,与青岛来客共餐,四菜一汤,先喝了白酒,青岛来客拿出一箱250mL的瓷瓶青岛啤酒,感觉像地瓜干子水,喝上脸发烧,还咯气。这是我第一次喝啤酒。以后的酒场,喝白酒后也掺着喝啤酒。 有天中午,我正独自吃饭,大嫂忽然挎个竹提篮来了,我给大嫂倒了杯水,说大哥没回来,让大嫂吃饭,她说一会儿就回家了。拿出2.9元钱来,说前几天家中有事项,你大哥身上没钱了,去采购站卖了个兔子,给你大哥买酒喝。说完就回去了。 晚上学校没上晚自习,大哥说去电影院看电影,放映《刘巧儿》,我没看,就去不到一里路的二姑家。 二姑父生病,脸黄肌瘦,说话有气无力的。爷俩坐在炕沿上喝茶,二姑父说:“你爷爷五十五岁老的,你父亲弟兄多,有个随后的。” 果然,这年冬天,四叔去世,正是五十五岁。难道冥冥之中真有因循迁移?还是自然巧合? 毕业时,我约了要好的同学孙启忠、梁铁军、卢春刚、刘志坚、徐建文、王宗顺、王明磊,吃了顿简单而愉快的晚餐。 大哥在酒间发言说:“你们都是很要好的同学,从现在起,告别学生时代,进入社会大学,将在各自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发挥自己的才能。在漫长又短暂的一生中,要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取长补短,共同进步、发展。使社会放心,叫父母省心,让家庭舒心,做一个具有良好道德情趣、有价值的人。”同学们报以热烈的掌声。虽然高考名落孙山,但我并没气馁纠结,就一般农村学生在一中上学,我的情况是比较好的,虽然当时说吃转粮,其实是将家中粮食存粮管所,折换粮票存一中食堂,吃大伙房。当时在生产队一人一年分个二三十斤粮,哪能够吃,是极不现实的。只得周六下午回家捎饭,夏季周三,家人到学校送饭,条件好些的,从大伙房打点菜。我们班一个学生,用大盐粒拌面粉,上锅炒了装在罐头瓶子里当咸菜。好处是一周不变质。那番艰苦,一想可知。我偶尔用十斤粮票,换七斤细粮票、三斤粗粮票。一斤细粮三个馒头。早饭是一个馒头,一两粗粮的玉米粥。现在想来,依然令人回味。 有时我也在公社建筑队伙房打饭菜,最难忘的是猪头肉拌黄瓜。现在在饭店吃饭,还点这菜。 屈指算来,离开学校快五十年了,我依旧怀恋那熟悉的校园,尊敬的师长,亲爱的同学。 至今还想上学,可惜时光不再…… 参加工作后,我也常到那三间房住,晚上看书学习,较为静谧。有时也约几个同学好友去吃一顿。大哥有时也去住几天。 1986年成家后,我不再去老马棚的三间房,大哥也于两年前调任洪凝镇建筑公司(前公社建筑队),将钥匙送交洪凝镇党委秘书。偶然路过,也过去看看曾住过的房子,再到陈书记家茶话叙旧。 2019年老马棚的房子拆除,改建居民商品楼,陈书记对我说:“当时你不交钥匙,也能分到一套半楼房。” 我至今也时常忆及或与熟人谈起,与大哥在老马棚的房子住过的八年岁月。 1982年,五莲农牧机械厂生产“宝山”牌自行车,大哥组织了十来个人的安装队,在农牧机械厂安装自行车,我上班的五莲果干厂放九个月大假,大哥对我说:“去安装自行车吧,挣了钱,还学门手艺,家有万贯不如一技在身。”当时修自行车就是技术。安装一辆自行车五元钱,每天能分到五至十元钱,在当时是比较高的收入了,工厂开产,还是回去上班。 八十年代中期,一个偶然,我与洪凝镇管工业的书记一起吃饭,谈起工厂放大假的事,书记说:“你是有技术人员,如不嫌弃,可找我来洪凝工业上班,十七家企业尽你挑选。” 我对大哥说了这事,大哥说:“洪凝工业,汪小蛤蟆多,我待了这么多年是知道的。”最后我还是去了洪凝工业所属的五莲县乳制品厂。 八十年代末,大哥的两个女儿已从学校毕业,央求大哥找熟人进厂上班。大哥不愿求人,便说:“到公司去搬砖、和灰,打小工。”俩女儿一听便撅了嘴。 大哥的大女儿凭考试招工,进厂当了工人,现在已是一家规模公司的高层领导了。 我找了我上班的服装厂厂长,厂长说;“老领导了,别人不安排,也安排你哥哥的闺女。” 大哥的二女儿进厂做了缝纫工,凭自己的不懈努力与刻苦学习,已在服装设计、裁剪、缝纫一条龙的厂服、校服、标志服制作销售方面独树一枝,目前是运作良好的一家服装加工企业的老板。 1989年的端午节后,大伯父仲跻仁突然去世,享年八十一岁。大伯父仰坐在炕上,一只手放在膝盖上,很安详。 大伯父年轻时很帅,做事利落,在集后村地主杨家很受信任,经年不回家,大伯母生活无望,只得另寻人家,以致没留下子嗣。 杨家的子女认大伯父为干爷,一直照顾生活,其子杨茂然,更是爷长爷短,照顾非常。冬年寒节,拂晓前将节日所需物品送至大伯父家。茂然的母亲给缝制的棉袄棉裤背搭子(手工衬衣),针脚细密均匀,布扣花结精致对称,堪称艺术,见者无不啧口称绝。 老年后的大伯父大多在大哥家,坐在一个高交叉子上,手拿一根手杖,吃饭时大哥给添杯酒,多了不喝。从没听到过哥嫂有半字怨辞。 大伯父的丧事,大哥为主办理,略作商量后,即安排直系亲属全部报丧,集后杨家更是首要。前来奔丧的人,务必于十点前赶到,以便举行各项丧仪。 杨茂然来时,眼含泪水,在灵前磕三个头,并说:“爷你一路走好!”丧服与我们八个叔兄弟的一样,九步三叩。 许家庄有看殡的风俗。起灵时,在哀乐声中,鞭炮齐鸣,人们纷纷走出家门,观看徐徐走过大街的灵车与哭丧的孝子贤孙。有的也跟着流泪,有的跟在送丧队伍的后面,直到村西桥头,灵车走远,才慢慢散去。有些街坊邻居在议论:“别看仲跻仁没儿没女,这殡出的,一些子女双全的,还办不到这水平呢!” 晚上,出殡的亲戚都已回家,自家人聚在大哥家。村委也派人送来烟酒,并带来书记的话:“丧事办的通俗全面,没给两委添丝毫麻烦,两委谢谢你们!” 大家边吃边喝,边议丧殡情况。大哥说:“听说怎(咱)家男的,过了55岁,都能活到80岁左右。今天大伯父老了,父辈们开始拆墙,弟兄们下步准备出殡上坟吧。” 当天的来宾与全家人,都在大哥家吃饭。大哥安排人采购饭菜,嫂子们齐动手,配菜的、烧火的,炒的炒、煎的煎、拌的拌,不用吩咐,自己找活干。宾客多,自家人不上桌,在院子的木板上吃流水餐,像吃大排档。每个客桌上只一个自家人,添酒倒水当主陪,吃喝不求好,但求吃得饱。所需费用,包括以后六次上坟祭祀、招待客人,全由哥嫂承担。我曾提出分摊,大哥不让,说办得到。 诚如大哥所言,父辈陆续去世,母亲2010年去世,是在世最久的先辈。每位父辈去世,都是留三日或二日的,大哥带头守灵,并说来吊孝的磕头,也要陪着磕头。 1997年父亲去世时,大哥说:“这几天,老听到村中有哭声,没料到应在咱家身上。”这话犹在耳畔。 随大哥出门办喜庆丧亡事很多,我最难忘的有两次: 1967年我八岁时,大姐订亲、出嫁,我都是与大哥去当大客。在大姐出嫁时的酒桌上,陪客见小孩,嚷嚷我喝了五盅酒,他们就不再劝了。 父亲与我说过:“我一辈子不会抽烟喝酒,在人事面前没的说没的道的,你要好好练习抽烟喝酒,别像我一样。”所以,我从五六岁便开始抽烟喝酒,这些大哥知道。 当时在酒桌上,陪客问大哥:“还让喝盅不?”大哥抽着烟笑道:“别看人小,还得叫大客。”大家哄堂大笑。大姐的公爹一咂嘴说:“啊要来,看来这表侄能喝一壶酒。” 六十年代后期,上水峪村的大姑夫病故,母亲让我与大哥一起去奔丧。路上大哥说:“你跟在我后面,我怎么做,你也怎么做。”又告诉磕头九叩礼的要点。 拜铭旌时,我在大哥后边瞌头,听到看殡的人说:“这小孩磕头还不糙唻!” 那时土葬,还没实行火化。当棺材下到坟圹子时,司仪让大哥抓三把土散在棺材上,因大姑夫没子嗣,只有四个女儿,而女儿是不能上林的。就是说,大哥替代儿子,埋葬了父亲。这是回家的路上问大哥才知道的。 有些事,大哥都作记录,也常说:“好脑子,不如个烂笔头子。”有事时,天刚亮,大哥即去叫门,说某某上坟或别的什么事,有时间一块去,直到见到你,答应去或不去,这才离开。 电话普及后,有事都打电话。 2001年清明的头一天,我在广州出差,忽然接到大哥电话:“村东南崖有咱太爷爷的几位兄弟与少亡坟,在山西路西侧,共有坟墓十一孔,这里已批为商住地,即将开始商品房土建,明早两点,我想迁移到村公墓。”我说我现在广州,大哥“噢”了一声便说:“那忙你的吧。”便挂了电话。 清明这天凌晨两点,我准时到大哥家,见已来了几位弟兄。大哥有些诧异而又天真的笑着问到:“广州这么远,你怎么回来得这么快?”有位兄弟说:“坐飞机呗。” 由于大哥准备充分,一辆三轮拉砖,大哥的三轮摩托车拉带有灵位的盒子,工程顺利,筑了不大的坟头,点香焚纸,鸣放鞭炮,圆满竣工。 大嫂在家做好了饭菜,弟兄们用酒洗了手脸,喷了身上,少喝点酒。大哥与四叔家伟忠大哥各自喝了两杯酒。大哥定了时间,再上个百日坟。 由于坟墓原在史家庄地面,早饭后与两位大哥到村委做了说明,负责接待的,是这村两委的仲崇国。 这一带村庄的人们,都有大年三十聚族上坟的风俗。有一年年三十上坟,大哥说:“凑钱买大鞭,过年上坟放,个人就不用捎带了。”我同意,并说:“多买礼炮少买鞭,燃放礼炮是趋向,每家一份。”后来大哥说:“多买炮是路子。” 年三十,在上坟的集合地,各人都主动交钱给大哥。从十元开始,二十元、三十元,到每年每家五十元。直到大哥去世头一年,已不能参加上坟时终止。 家中出现矛盾与纠纷,都找大哥排解,大哥也公平、公正、合情合理地予以解决。外人都说:“他们家族很义合。” 进入九十年代,在村头山西路东,近200米处的岭头果园里,大哥陆续盖起了六间屋,一溜猪圈及鸡舍、鸭棚免子窝,着重发展家庭养殖业,收到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站在养猪场的院子里,环视四顾,对面是灵山与大青山,东面是分流山,北面是昆山,整个小县城一览无余,尽收眼底。岭下向东是洪凝河,河东是五莲汽车站,直线不足二里路。每年正月十五,在这里观看县城的烟花灯火,是最佳选择。大年初一,拜完年的弟兄们都在这里聚餐。 有一年夏末秋初,在养猪场后边不远处的深沟里,大哥发现了一个鬼鬼祟祟的中年妇女,旁边树上还拴着一头牛。这里沟深树密,不近前是看不到的。忙喊来大嫂走近前,见这中年妇女解下牛纲绳要走,大哥制止,请其把话说明再走,并打电话让居委会来人。中年妇女吱吱唔唔,环顾左右,不肯说明情况,大哥当场报案。 办案人员立刻赶到现场,随即将中年妇女控制。原来,当天早晨公安局接到杨庄报案,夜里被盗走耕牛一头。不承想被大哥捉了个正着。 经过突审,公安部门很快将另外两名罪犯抓获。 原来女贼藏身处东边,洪凝河右岸,有一条土公路,知道的不多,走的人更少,等天黑后来车拉走,卖一万多元。 大哥大嫂夫妻擒贼,一时传为佳话。 有位兄弟埋怨大哥,说这事办得欠妥,如果犯罪分子报复你怎么办?大哥不同意这话。 随后,公安局一位领导来,对大哥表扬并感谢。还送大哥一杆附有持枪证的枪支,并说要保持一个老党员、老干部的作风,继续为社会的安宁作出贡献。 著名的五征集团在许家庄村后,村周边有很多为五征配套的车辆零部件生产厂家,其中就有同学刘志坚与梁铁军。铁军的厂家迁许家庄后,找大哥看门,因为知道大哥为人亢直正气。大哥到厂看了后说:“白天上班的人多,不用看,晚上我给照看着。”说到工资时,大哥不要,最后每月600元,要个烟钱。 2010年,县里将猪场所在的这片山场收为储备地。猪场中的房屋猪舍等,补偿了十几万元。这是大哥一生中最高的经济收入。 大哥在洪凝建筑总公司任职多年。2000年末,撤乡并镇,企业彻底改制给于同生。洪凝三十年资产积累,使于同生一夜之间成为新生的资产阶级暴发户。中层以上人员全部办理退休手续,有施工资格证书的项目经理将证书留公司。后来据副总张善松不完全统计,当时的资材值两个多亿的人民币。 虽然办了退休,但没退休金,真是咄咄怪事。一些副总、经理,纷纷找大哥苦诉冤屈,要求上访。经大哥耐心说明,选举六人,以大哥为首,到洪凝镇党委反映。 洪凝镇党委书记杜树厚是的我同学,我向他反映后,他客气地说:“需要向县委、县政府汇报。”让我回去等候消息。 之后,杜树厚调日照市任职,六人中的激烈人物张善松也已去世,此事不了了之。 据确切消息:于同生已于两个月前暴毙。 2011年7月1日,建党九十周年时,一市委副书记到大哥家慰问老干部、老党员,并赠送了3000元现金、证书等。 在村里开党员会,大哥总是第一个到会,人们都说:“仲伟习是标准的共产党员。” 2014年夏,大嫂去世。 相濡以沫五十年的老伴去世,使大哥无所适从,似乎有些彷徨呆滞。 我怕大哥孤单,时常到猪场的住处陪伴大哥。有时女儿女婿陪大哥吃饭,他心中很高兴,喝酒较前更多了,可能是借酒的麻醉,睡的沉香吧,但不知醒来又如何呢? 一天下午,日薄西山,晚霞满天,我到大哥住处,见大哥蹲在岭头抽烟,夕阳的余晖照着他已见瘦削的脸庞。似在沉思默想。快到眼前时才发现,抽烟后进屋喝茶,邀大哥一起吃。大哥说饭菜不少,大嫚二嫚都来送,你也在这吃吧。我退了约餐,陪大哥喝酒。尽量谈些愉快的往事。大哥兴致高,喝了不少酒,十点多才离去。 对编纂《仲子世家谱·五莲支谱》及为石场、洪凝两处始迁祖立碑,大哥都非常拥护、支持,积极捐款并参加各项活动。他说:“这是办的正事,要办好。”我在搜集《五莲许家庄的仲氏庙》素材时,大哥说:“听老辈人讲,原来许家庄族人过年上史家庄请家堂,建庙后,史家庄族人上许家庄请家堂,有事也在庙里办。可惜,砸庙时咱们都没在家。” 储备地中的房子,2016年才拆除,开发了海棠湾生活区,大哥搬回了村中的老房子。不久,又搬到二女儿崇花的服装厂住,顺便看门,距大女儿崇爱家也不远,照顾方便。我也时常去与大哥喝茶叙话。 大哥的酒友不少,其中有个小偷小摸的何兆运,时常来喝抹酒吃白食,被我和两个侄女斥责几次后,窥视我们不在时还来,还领了个贼眉鼠眼的妻子,后被发现,又遭呵斥,这才不见。 尽管两侄女对大哥关爱有加,呵护倍至,但大哥的身体状况还是每况愈下。我知道,任何人都无法替代大嫂在大哥心目中的位置,但这又是无可奈何的事。 2021年,年三十上大坟时,我打电话给大哥,他说:“你们去吧,我已走不动了。”我心里酸酸的,暗叹时光易逝,不觉老之将至。 2022年正月初的一天上午,我接到侄女电话,说:“小叔快回来看看吧!”言及过年前后来看望其父的人送的烟、酒、奶及保健品,被摔手来的小偷何兆运夫妻全部偷走。 我一听,气愤地火冒三丈,立刻赶到大哥家,看了监控视频,物品在被玻璃罩盖的院子里被这无耻夫妻几趟搬走,我即让人打电话,限十点前送还,否则报案。 一会儿,何兆运夫妻开破三轮送回一些,侄女说:“还有,没送完。”何兆运又拉回一趟。这时的大哥已卧床不起,无法下地。 我对何兆运道:“年前你刚因偷盗被拘留释放,现在又做案,真是死不改悔。如果报案,最少再拘留十五天,罚款5000元,从此不准再来!” 何兆运被我的一个同学打了两个耳光,他自己又打了自已几个耳光,说:“你们大人不计小人过,别跟我一般见识。”说罢,这对狗男女,开着破三轮,灰溜溜地走了。 尽管两个女儿女婿照顾得无微不至,日夜相伴,终因无力回天,大哥还是安详地魂归天国。 夜里守灵,我们谈了些大哥大嫂的往事,特别谈了退亲又送亲一事。 亲朋好友都来送大哥最后一程。出殡时,在鞭炮与哀乐声中,我与伟忠大哥在灵车左右,用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陪伴大哥,最后一次缓缓走过许家庄大街。 大哥殡葬后的第二天晚上,我刚上床躺下,正想着两个闺女把大哥打扮得舒服地去找大嫂了。忽然接到二侄女崇花电话:“小叔……”话未说完,她已泣不成声,不能自已,只从电话传来哽噎的啼哭声。 估计是在她父亲的老房子里,因往日这时,都在这里伺候父亲,达一年之久。今晚到此,睹物思父。忽忙到屋一看,果然如是。 我没说话,站在一边,很久后才劝说道:“都说百日床前无孝子,你姐妹俩伺候你父已一年之久,从未懈怠,心力已尽到,人力亦难为,也是人生必然,你父找到你母亲,应该是快乐的。过‘五七’后,你与你姐一起把你父亲的遗物,除留下的,全部扔掉或烧掉。以后无事,不要独自来了。” 斯人已去,风范长存。亲爱的大哥,我们永远怀念你! 山东五莲仲伟祥 2024年8月
|  |Archiver|小黑屋|手机版|华夏仲氏网
( 苏ICP备2021045915号 )
|Archiver|小黑屋|手机版|华夏仲氏网
( 苏ICP备2021045915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