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即注册
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没有账号?立即注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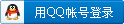

×
“鲁国卞邑有位游侠,名仲由,字子路,一日立意要将近时颇有贤者之名的学匠孔丘羞辱一番。” 中岛敦《山月记》中的名篇《弟子》以这样的语句开头。这篇小说几乎毫无虚构,全部使用史传中已有的关于子路的记载,却勾勒出一幅不凡的人物肖像,让人不得不感叹中岛敦虽为日本人,对中国先秦的典籍却是如此详熟,更有着独到的见解。 但是,小说中把子路塑造为一个质朴(略有点蠢萌)的勇士,“和精明的实干家比邻而居的大孩子”,总是固执坚持自己的想法,时而站在孔子的对立面。这一人格或许大体符合子路在史传中的形象,也颇有几分趣味,但不得不说,对子路的理解还是浅了些。 浪漫派的文学批评,其宗旨是“为作者完成作品”(本雅明《浪漫派的艺术批评概念》)。那这里我就要补充一些中岛敦丢弃的史传材料,为作者、也为广大读者,完成子路。然后我们就会发现子路的伟大,他从始至终都是一个极端重视契约论的侠客。他是中国第一个这样做的人,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唯一一人。
【1. “策名委质”的契约论】 有人说中国人没有契约精神,有人说中国的侠客“重然诺”“讲信义”,就是一种契约精神,更甚至有武侠作家试图用小说来讨论“侠客的契约论”。其实只要我们细读子路,中国上古的契约论思想自然就能浮出水面。 姑且按照中岛敦的顺序来说,在开头试图羞辱孔丘不成,反而被孔丘折服之后,子路决定拜师:“即日起,子路执弟子礼进入了孔子门下。” 我们对比一下史料原文:《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子路后儒服委质,因门人请为弟子。” 子路脱掉了他之前奇怪的“野猪武士”(冠雄鸡,佩豭豚)的打扮,改穿儒服。这之后,重要的“委质”之礼却被中岛敦省略了。在这里,《史记索隐》引服虔注“古者始仕,必先书其名于策,委死之质于君,然后为臣,示必死节于其君也。”同样《国语.晋语九》亦说“委质为臣,无有二心。委质而策死,古之法也。”可见,子路对于孔子所行的礼,并非现代人理解的“弟子规”,而竟是君臣之契约。这种契约在春秋时代十分常见(见杨宽《贽见礼新探》),不仅表示君臣关系的确立,更表示自愿为其服务、劳役,甚至是生死相随地保护之。而子路对孔子,则移君臣为师徒,通过“策名委质”的礼仪确立了他与孔子之间的名分与义务。所以中岛敦在后文中假想子路“从为斯人(孔子)洒泪的那天起,便下定了决心,要做一面在浊世中保护斯人的盾牌”“为了夫子愿意抛弃性命的首先是自己”,却没有明白,这一觉悟正是子路早在入门之初就与师傅正式定下的契约。 而子路用生命与死亡践行契约的旅程才刚刚开始。
【2. “久要不忘平生之言”的契约论】 中岛敦反复提到,子路一直在坚守一件“世上顶要紧的东西”。“在它面前,死生尚不足论,更不用说区区利害。侠,这个字眼略嫌轻率。信呀,义呀,又过分道学气而缺少自由灵动之感。”子路无法清楚地言说,但是“名字无关紧要,对于子路来说,那近似于一种快感。” 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听起来很像是武侠小说《英雄志》里卢云遵守的那个“正道”:“正道,就是做对的事情。正道之界,岂容一步寸让?”但如果真的如此,为什么子路认为“它和孔子所讲的仁大相径庭”“孔子最初不是没有想要矫正他这个犄角,可后来就放弃了。” 它真的如此复杂难言,又和儒家的理论相悖吗?非也。这个东西其实很简单,就是契约论、契约精神,而且孔子也完全不反对。 中岛敦似乎没有注意到,子路在《论语.宪问》中曾问过孔子,如何能成为完人? 孔子答道:有臧武仲的智、孟公绰的廉、卞庄子的勇、冉有的艺,然后再以礼乐文饰,便可以成为完人。之后,孔子又怕这个要求太高,子路做不到,便说了一句极其重要的话:“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 要,约也,周代契约的一种形式。何晏《论语集解》、朱熹《论语集注》等书都认为:“久要,旧约也。”守旧约、重诺言,见利而不忘义、有危而不惜命,如此可以为完人。这就是孔子对子路的要求,也正是后世侠客的契约论。 孔子前面所说的臧武仲、孟公绰、卞庄子、冉求等,都是他专门用子路所熟悉的人来激励他(参见《朱子语类.论语二十六》)。尤其是卞庄子,他是子路故乡的英雄,以刺虎之勇而闻名,在子路心中,卞庄子之勇应该一直是他的榜样。然而孔子害怕子路做过头,所以经常打压他的蛮勇,比如他对子路说的:“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这明显就是针对子路的崇拜对象而发,怕的是子路以后“不得其死”。但是他也明白子路无法完成他的全部要求,于是便把“勇”提炼出来,升华成了上文的侠义准则。 子路果然做到了这一点。后面我们会看到,即便他最终仍不得好死,却也正是出于践行这一准则的结果。我们不知道这算不算是“完人”,但是子路很好地完成了他的一生。
【3.“子路无宿诺”的契约论】 遵循孔子所说的“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子路做到了“无宿诺”。这种对诺言的极端尊重,子路是第一人。检索先秦典籍我们可以发现,“诺”本是一句口头语,等于说“OK!好的!”除了某某人曰“诺”之外,在古书中,常见的只有“许诺”“敬诺”两个动词。诺言作为一个独立的名词概念,几乎是不存在的。只有到了汉代,才出现了“然诺”一词,如“季布重然诺”,而子路是提出和践行这一概念的第一人。 这里我们简略回溯一下中国古代契约的发展历程。从最早的结绳为“约”(约,缠束也),发展为后来的书面之“契”(契,大约也),周代的契约已经有异常丰富的形式(傅别、书契、质剂、要会等),但往往是专门针对某种权益问题的文书。而广泛使用的一般性契约,则是“盟”。盟可以是君主之间的会盟(《左传》之盟),可以是君主与臣下之间的盟约(《侯马盟书》),也可以是私人之间的盟誓,孔子众人被困于蒲地时,当地人就逼着孔子与他们立盟,到今天我们还把爱情与婚姻的约定称为“海誓山盟”。盟,上面是日月神明,下面是盛血之皿,杀牲歃血、告誓神明是为“盟”,仪式的神圣性毋庸置疑。如果有人怀疑中国古代没有契约论,契约不具有神圣性,则“盟”之一字可为最好的反证。(参见吕静《春秋时期盟誓研究》) 从子路开始所践行的“诺”,是一种微型的、口头的、不流血的盟约。在春秋之后漫长的历史发展中,“盟”早已丢失了它的神圣不可侵犯性,而“诺”则为侠客所极度重视,保留了下来。中岛敦写道:“子路生平独立不羁,以甘居人下为不洁,是一位一诺千金的好男儿。”他却没有注意到,“一诺千金”的季布不过是子路的继承者,而子路的“诺”是建立在更为深厚的契约论基础上的。 这里根据的史传原文是《论语.颜渊》:“子曰:片言可以折狱者,其由也与!子路无宿诺。”历代无人能解释清楚,“片言折狱”和“无宿诺”有什么联系,两者为何在一句内出现? “片言”在后世被解释为“单方面的言辞”甚至是“只言片语”,“折狱”则被解释为“断狱”,这样子路就成了个简单粗暴的莽汉。然而其实这里写的是古人用盟誓以审判的传统。 誓,从言从折,《说文》曰:“以言约束也”。《康熙字典》引《六书统》:“以言折其罪也”。所以,“誓”是“折狱”的方法,如《周官.秋官司寇》云:“有狱讼者,则使之盟诅”,用现代话来说,就是在诉讼争端时的一种“神意审判”。根据《先秦判决中的“誓”与“比”》(邹芙都、查飞能)一文研究,西周以来用“誓”来进行司法审判的案例屡见不鲜,如《(亻賸)匜》“牧牛则誓”《(鬲㐄)比鼎》“攸卫牧誓曰”和《散氏盘》“武父则誓”等都是明证。在《墨子.明鬼下》中更有一起“中里徼案件”的详细记载,让我们得以一窥“誓审”的真相: “昔者,齐庄君之臣有所谓王里国、中里徼者,此二子者,讼三年而狱不断。齐君由谦杀之恐不辜,犹谦释之。恐失有罪,乃使之人共一羊,盟齐之神社,二子许诺。于是泏洫(扌惡)羊而漉其血,读王里国之辞既已终矣,读中里徼之辞未半也,羊起而触之,折其脚,祧神之而槁之,殪之盟所。当是时,齐人从者莫不见,远者莫不闻,著在齐之春秋。” 王里国、中里徼争讼三年不休,于是只好进行神意审判。二人各自信誓旦旦,说自己无罪。王里国念完誓辞之后,并无异状。而中里徼才念到一半,已经献祭而死的羊却跳起来折断了他的脚,他于是被杀。这就是古人所相信的“誓审”,在后来西方基督教世界也经常进行。 而“誓审”仪式之中,必须有公证人进行主持,公证人本身也必须发誓(如《包山楚简»第137号简,处理“余庆杀人案”时,“执事之人为之盟,凡二百人十一人。既盟,皆言曰:[...]”)。所以公证人的可信度,对于“誓审”的公正性也非常重要。子路因为“无宿诺”,其公信度闻名天下(详见下文),所以孔子才会说,只有你可以“片言折狱”(用誓裁决)啊!(*而这和孔子一贯的法律思想也相契合:“以直报怨。以德报怨,何以报德?”“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必也使无讼乎”“有父子讼者,孔子拘之,三月不别”。法之施行,在“直”而不在“讼”。) 只有明白此节,我们才理解《论语.颜渊》记录“子路无宿诺”的深意,一个人如果连最小的口头承诺都可以当天完成,那么不管是“誓”还是“盟”,他必然会以死践行。这样的人,才是真正可信的。虽然“神意审判”这种手段,今天看来是非常落后了,但其本质来源于对契约神圣性的深信不疑。而子路本人,则成为这一神圣性在世俗间的象征。
【4.“千乘之国,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的契约论】 子路的信义得到天下公认,另一个著名的例子见于《左传.哀公十四年》: “小邾射以句绎来奔,曰使季路要我,吾无盟矣,使子路,子路辞,季康子使冉有谓之曰,千乘之国,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对曰,鲁有事于小邾,不敢问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济其言,是义之也,由弗能。” 小邾国的大夫射投奔鲁国,欲献上句绎城,此人对鲁国说,我不用和鲁国盟誓,只要子路来和我定下契约,就足以为信了!季康子不禁感叹道:“千乘之国,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由此我们可以发现,人们对子路的信赖,竟超过了对国际之间“盟”的认可;城池领土的交割,竟然可以因子路一人的誓言来完成,这真是侠客契约论的极致了。 不过,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子路对于盟誓的极端审慎。他对此事表示断然拒绝,因为对方是不义之臣,是以无法与其盟誓。中岛敦在小说中对此有详细描写,“认识子路的人听说了他的这些话,都不由得微笑了。”这里强调的还是子路的执着、忠直,却少了些对契约精神的重视,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
【5.“子路治蒲”的契约论】 中岛敦对“子路治蒲”一事,也述之甚详,表现了他不一般的洞察力。不过这件事对子路一生的重要性,他还是差一口气没能点破。让我们完整地透视此事: 小说中说“这里自古以来民风凶悍,子路自己就曾经追随孔子在这里遭受过暴民的袭击”,其根据的原典是《史记.孔子世家》:“(孔子)过蒲,会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车五乘从,斗甚疾。蒲人惧,谓孔子曰:‘苟毋适卫,吾出子。’与之盟,出孔子东门。孔子遂适卫。子贡曰:‘盟可负耶?’孔子曰:‘要盟也,神不听。’” 小说中省略了孔子背盟的关键情节。蒲人让孔子立誓不去卫国,才放他们离去,结果孔子转头就去了卫国。子贡质疑这一行为,孔子便解释道:强行要挟之下所订立的盟约,毫无神圣性可言,所以不用遵守。这是孔子自己的契约论解读,我们会在下文重点讨论,这里先跳过。 而有了这一“背盟”之事,蒲地人对于孔子及其弟子的态度,自然是极端厌恶。所以后来子路去卫国做官,受命治理蒲邑的时候,孔子是满心担忧的。中岛敦的小说中,他特意对子路说:“蒲多壮士,极难治也。然恭而敬,可以摄勇;宽而正,可以怀强;温而断,可以抑奸。”(这段话基本是照抄《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接着:“三年后,孔子偶然经过蒲地。刚进入领地,就说道:‘善哉,由,恭敬有信。’接着走进城邑,又道:‘善哉,由,忠信有宽。’等最后来到子路的宅邸前,他又说道:‘善哉,由,明察有断。’”(这里也基本是照抄的《孔子家语.辨政》和《韩诗外传.卷六》)。 但是我们并不明白子路如何对蒲人完成了大改造,孔子又为何如此大加称赞?当时子贡就感到不解,“夫子未见由,而三称善”,这是一向不支持子路政治理想的孔子,难得的一次赞誉。要知道在《论语》中,我们基本只听到孔子对子路的贬抑,更有“门人不敬子路”这样令人伤心的记载。 不过只要我们细读文本,就可以发现,子路并不是完全按照孔子“恭敬”的方法去治理的,他教导蒲地人民的是“忠信”,这是孔子没有对他说的。孔子发现子路完成的比他预想的更好,正是因为有了“忠信”,所以才超乎寻常地“三称其善”。 何谓忠信,符契曰信、信誓旦旦,言必信、行必果,民无信不立,“信”正是儒者契约论的最高道德。而“无宿诺”“千乘之国,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的子路,正好是这一标准的楷模。对“好勇”的蒲邑加以升华,便是“忠信”,子路把孔子教导自己的方法,转用到了蒲地人民身上。 蒲在卫国,属于卫都濮阳的郊邑,子路治理此地的结果是“卫地有桑间濮上之阻……周末有子路、夏育,民人慕之,故其俗刚武,上气力。”(《汉书.地理志》)卫国的侠风,由子路开创。后来卫国迁往野王,于是“濮上之邑徙野王,野王好气任侠,卫之风也。”(《史记.货殖列传》)这一风气一直保持到汉代,于是司马迁、班固都对此特别强调。 然后我们就会发现,战国时的刺客聂政,被濮阳严仲子收留,为其报仇;汉初的濮阳周氏又帮助被通缉的大侠季布逃亡;卫人荆轲,曾在濮阳事卫元君,他刺杀秦始皇之时,口中念念有辞,是“必得约契以报太子”;汉代的直臣汲黯为濮阳人,“好学,游侠,任气节,内行修絜,好直谏,数犯主之颜色”(《史记.汲郑列传》)濮阳一带,实在是战国直到汉代的侠客中心之一。《汉书.游侠传》说:“布衣游侠剧孟、郭解之徒…虽其陷于刑辟,自与杀身成名,若季路、仇牧,死而不悔也。”子路在卫国的治理,致使侠风大兴,更成为后世游侠之标榜。太史公说游侠“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完全就是子路的写照。千载之下,朱熹在《朱子语类》中依然赞叹,子路大有“战国侠客气象”。 《荀子.大略》又记载:“齐人欲伐鲁,忌卞庄子,不敢过卞。晋人欲伐卫,畏子路,不敢过蒲。”可见子路治蒲大获成功,他也达成自己他心中的理想人格,如同偶像卞庄子,并进一步超越了他,成为后世所有侠客的偶像。
【6.“民人社稷”的契约论】 于是我们不得不反思孔子对于子路的评价。对自己的政治才能,子路早有自信,他在《论语.先进》中说过:“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当时孔子的态度是“哂之”。 然而同样是三年,子路治蒲却大获成功、名传天下,确确实实地使其“有勇而知方”(方,何晏注“义方”,道义也)。这必然震撼了孔子,所以他才会赞口不绝。后世儒生多强调“学而优则仕”“温良恭俭为君子”,殊不知“不读书”的子路,依靠着儒家精神隐含的契约论、正义论,照样能治理好人民,这倒是和西方社会的精神暗合。 回头再看子路不读书的缘由,便可以发现他自有其理路。《论语.先进》“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 为何这里民人、社稷两个名词,足以代替“读书为学”?历代注家并未站在子路的角度对此加以解读,然而这里我们仍然能看出契约论的精义。 社、稷,乃祭祀之所,所以是“盟誓”进行的重要场所(如前文《墨子.明鬼下》的案例中即“盟齐之神社”,《左传》亦数见)。《左传.定公六年》讲阳虎掌权时,“又盟公及三桓于周社,盟国人于亳社,诅于五父之衢。”这里,他和鲁国的统治者们在周社结盟,因为他们是周人;又和国人,也就是鲁国的殷民遗族,在亳社结盟;最后,又在都城的五父之衢设“诅”(大事曰盟,小事曰诅,可视作小型盟誓),对象很可能是周人平民(参见杜正胜《周代城邦》)。他构建自己的权力基础,即通过于这两盟一诅的契约。他必须分别与不同人群定约,来编织自己的权力网络,这其实已有不少社会契约论的含义了。同样,《左传.襄公三十年》,郑简公为了巩固国政,“郑伯及其大夫盟于大宫,盟国人于师之梁之外”,也是分别和大夫及国人会盟,如此情况在《左传》中比比皆是。 战国初期的《墨子》,更是直接说“君臣萌,通约也”(萌,民也。君、臣、民,通其契约而形成国家),《墨子.尚同上》中则言“一人则一义,二人则二义……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药相亏害……天下之所以乱者,生于无政长。是故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这里的“选天子”之逻辑,已经和霍布斯的社会契约论相同(人对人是狼,因自然定律而需要社会契约)。可见与人民结盟通约,已经不仅是当时政治的常态,更有进一步上升到理论层面的可能,只可惜这一理想却被战国的兼并战争所打断了。 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子路说及“民人、社稷”的意义。《论语集解》对子路的言论进行解释“言治民事神,于是而习之,亦学也”,说领导民众敬事神明,也是一种学习,已经算是很有见地的解读了,却未能上升到契约论的高度。我们从子路对于忠信、契约、盟誓的重视,足可以理解,子路原话的意思是,领导人民盟于社稷,才是国之大事,何必一定要读书呢? 后世儒生的理想人格,大多是书生治国,用精英文官阶层,上辅天子,下安百姓,这固然值得敬佩,但却不是政治的唯一途径。政治,英文politics,德文Politik,均来自于古希腊文polis,城邦。故政治实为城邦政治、市民政治、国人政治(国,城也,Staat=Stadt。国有“国人”,如city之于citizen,Burg之于Bürger。Polis一词,则兼有Stadt, Staat, Burg诸义。)原本不需要文官阶层在其中穿梭代劳,按照先秦的契约论,一样可以组成国家、政治。子路就是这一原始契约论的人格表率,可惜竟被埋没,惜哉。
【7.“要盟也,神不听”的契约论】 到最后,子路陷入卫国政治乱局,壮烈而死。中岛敦小说中如此写道:“敌人的长剑刺入了肩头,血花迸溅,子路倒在地上,冠掉了下来。……他拾起冠,把它端正地戴在头上,并迅速系上缨带。在敌人的白刃下,遍身是血的子路用尽最后的力气叫道:‘看吧,君子是正冠而死的’。” 这是史传热衷刻画的“结缨而死”的场景,子路的行为颇有武士之风,中岛敦作为日本人会被子路所吸引,大概也有这个原因吧。但是对子路守节而死的文化解读,历来还是不够深入。 节,竹约也。守节即守约,子路守的是与孔悝的君臣之约。蒯聩挟持孔悝,让他帮助自己政变篡位,“迫孔悝于厕强盟之,遂劫以登台”(《左传.哀公十五年》),子路于是为了救他而战死。孔悝其实没有生命危险,不过是换一个主子罢了,子路却因此付出了生命,似乎死的有点不值。但是,这里我们如果回溯孔子“要盟也,神不听”的逻辑,便知道子路是为了自身的契约信仰而死。 我们回顾一下上文,孔子困于蒲,被逼立盟,孔子假意答应,事后则不顾盟约。他的解释是,强迫的盟约没有意义,神不会接受的,这里强调的是契约的自主精神。如果契约并非自愿,则也不具备神圣性。所以孔悝虽然已经与蒯聩结盟,但子路却不承认也不允许,故而为之战斗而死。子路又一次践行了孔子的教诲。 在孔子门下时,子路多次为了师傅打斗(如《说苑.杂言》《韩诗外传.卷六》),用直接和强势的手段面对反对者,所以孔子说“自吾得由,恶言不闻于耳。”(《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大概真如中岛敦小说中所假想的:子路把反对者不是打服了,就是吓跑了…… 当然,困于蒲那一次出战的是公良孺而非子路,但我想以子路的脾性,面对不义之盟肯定也是要抗争到底的。由于孔子的压制和缓和,子路才能一次次全身而退,到了蒯聩之乱时,却没有了孔子在旁回护,子路终于慨然赴死。这是孔子早已预见到的:“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论语.先进》)但子路为了自身的信念而死,成为侠客、武士的楷模,未尝不是一种善终。他完美地完成了自己的一生,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是可谓成人!
【8.“儒侠”的契约论】 如上可见,子路一生种种行为,都是他契约论的证明。策名委质,是师生契约。结缨而死,是君臣契约。久要不忘平生之言、无宿诺,是私人之间的契约论。民人社稷之言、以忠信治蒲地,是政治上的契约论。片言折狱,是法律上的契约论。千乘之国,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是外交上的契约论。方方面面,子路都以契约为准绳,践行终生,这就是后世“儒侠”的范式。 (*儒侠之名虽不见于儒书,然民间自有传承,见章太炎《訄书.儒侠》之议论。子路,鄙人也,与”巨盗”颜涿聚为友,可能自己本也是个江湖人。漆雕开、北宫黝之流,原宪、公晳哀之辈,乃至于澹台灭明“以诺为名”,皆早期儒侠之羽翼,此处暂不展开。) 我一向坚持,早期儒家之中,不独有颜回、曾参之类爱读书的“儒生”,尚有子路之“儒侠”、子贡之“儒商”,子夏之“儒师”(传经致用,为王者师),冉有之“儒将”(《左传.哀公十一年》领导儒门子弟大破齐军),甚至是注重神话学的宰我,类似宗教领袖的有子。这些人都给“儒”提供了各种各样的范式,证明“儒”有无穷可能,绝不是后世那种迂腐的刻板印象。“六艺”之中,取其书、乐当然足以成为儒生文士(其实后来儒生连音乐修养也放弃了),取其射、御便是儒侠武士,取其礼、数又是儒商政客。“儒”的多样性,沉埋已久。 后来章太炎等人认为,《礼记》中有一篇《儒行》,就是后世“儒侠”的纲领文件。其中说道:“儒有不宝金玉,而忠信以为宝……儒有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儒有忠信以为甲胄,礼义以为干橹……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诸侯……儒有不陨获于贫贱,不充诎于富贵,不慁君王,不累长上,不闵有司,故曰儒。”本文确实有一种顾盼自雄的豪气,但可惜对于儒侠的契约论却强调不多,只是将其隐藏在了“忠信”的概念之中,后人论《荀子》亦然(参见罗哲海《轴心时期的儒家伦理》)。 不过这篇《儒行》好歹是大声喊出了“儒”字。从《论语》开始,儒家经典不敢言“儒”,就是一件咄咄怪事,这我已在《谜之智者:宰我》中另文述之。放之其他门派,道家不言道,法家不言法,名家不言名,成何体统?!《礼记》一书中,除了《儒行》中一口气用了24次“儒”之外,其他部分仅使用两次,还都是“侏儒”之儒。难怪《儒行》篇在最后说道: “今众人之命儒也妄,常以儒相诟病。……终没吾世,不敢以儒为戏。” 这一篇章的作者,想必对儒生们的呆板怯懦是极度不满的。在孔子与子路的关系上,早已表现出这种“武士”与“文士”的对抗。子路多次否定孔子的政治选择,当面质疑,孔子也被子路逼得手足无措、百口莫辩(《论语.雍也》“夫子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可见在颠沛流离之中、长年怀才不遇的困境之下,即便孔子也有时如丧家之犬,心中忧惧,难免病中呻吟或是顾影自怜。这些时候,子路便是孔子的诤友和检验者。他其实扮演了孔子体内勇直刚猛、武者气质的一面,时刻与那怯懦虚矫的文人习气做斗争。故而《尸子》记载:“仲尼志意不立,子路侍。”这才是孔子内心深处,希望自己即便流落东海,依然能有子路追随的真正原因。(《论语.公冶长》“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 中岛敦在小说中写道:“受教将近四十年,(孔子与子路)中间的鸿沟,还是无法可想。”其实并不了解双方之间的这种良性对抗。子路死后,孔子如遭重击,很快也魂销命殒,便是因此。《论语》编修之人,乃是曾子领导的门人,然而“门人不敬子路”,所以对子路的信念、力量毫不了解,后学注解《论语》时,更加不知所谓,把仅有的一些蛛丝马迹全都忽略了,令人痛心。 最终继承了“儒侠”精神残余的,只有后来的江湖游侠,他们接受了子路私人层面的契约论,如“重然诺”“轻生死”“主忠信”“讲义气”等等。《论语.公冶长》中,孔子让弟子们说说自己的志向,子路第一个说道:“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他待朋友之无私(如颜涿聚),济百姓之公义(如子路治蒲时,自掏腰包救水灾,见《说苑.臣术》《孔子家语.致思》)等行为,也被侠客反复效仿。《韩诗外传.卷九》载“子路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不善之。子贡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则引之进退而己耳。颜回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亦善之。“此处可见子路的处世哲学为“直”。他的“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不善之”和墨子的“爱人者人恒爱之,杀人者人曰可杀”再到民间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都非常强调绝对的公平与孤直,有一种作用力等于反作用力的自然法则在里面,这也是为后世广泛继承的部分。不像那些儒生,多遵从的是颜回“人不善我,我亦善之”的博爱与仁弱,实则违背了孔子的“以直报怨”。 但是,子路在政治、外交、法律层面上的契约论,却再也没有人加以申发。然而这些正是西方所谓的“契约精神”。这种精神,其神圣性表现在上帝与人的《旧约》《新约》之中,和商业文明结合,则发展为现代文明的信用与信托机制,和政治文明结合,则表现为全套的“社会契约论”和“人民主权说”,如此种种,其实中国古已有之,不必他求,只是或含苞待放、或胎死腹中,今人多不知矣。中岛敦的《弟子》如果能从这个角度解读子路,方知子路所求之大。读者如果能从这个角度重看《论语》,方知儒家之潜力与活力。本文之批评如果能达到这个效果,才能说是子路之“完成”。
|  |Archiver|小黑屋|手机版|华夏仲氏网
( 苏ICP备2021045915号 )
|Archiver|小黑屋|手机版|华夏仲氏网
( 苏ICP备2021045915号 )